[内容提要]:曹氏归义军时期,由于曹氏家族与于阗王族的联姻政策,使得敦煌与于阗进入到一个密切交流的时期,大量于阗人活动在敦煌。在这个时间段中,敦煌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李圣天、皇后曹氏等于阗王族的供养像。通过对这些供养像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原地区的服饰制度在敦煌保留下来,于阗王族们的礼服明显模仿着汉地帝王、皇后的服饰,于阗太子所着的常服也与敦煌当地居民相同。在佛事活动上,于阗人与敦煌民众也是趋于一致,写经、造像并无二致。体现出于阗王族在服饰制度、佛教信仰方式上趋于汉化。这种汉化的倾向甚至西传到了于阗本土,使得晚期于阗出现了汉风明显的图像。
[关键词]:于阗王族供养像;李圣天;服饰制度;佛事活动;汉化
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阗王李圣天遣使入中原朝贡,高祖石敬瑭随后遣使张匡鄴、高居诲前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此时,距离于阗陷于吐蕃统治、中原王朝与于阗中断官方联系已经将近150年。[1]当高居诲一行人历时两年到达于阗见到李圣天本人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2]
这一描述也符合敦煌莫高窟98窟中于阗王李圣天的形象,显然,这位笃信佛教的于阗君主在汉使到达之前,就已经深沐汉风。在唐王朝的势力撤出于阗,又经历过吐蕃长达80余年“编发易服”[3]的统治之后,需要考虑到934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嫁女于李圣天。之后直到11世纪初,于阗灭亡之前,于阗与敦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需要将敦煌纳入视野之中。在敦煌,除了文书的记录之外,还有不少于阗王族的供养像出现在石窟之中。这些供养像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呈现出汉文化对于阗王族的影响?本文试从图像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敦煌石窟中的于阗王供养像
曹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家族与于阗王族结成姻亲关系,曹议金嫁女于阗王李圣天,之后曹延禄又娶了于阗公主李氏。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于阗人往返于沙州、于阗之间,除了留下大量的文书记录之外,作为曹家的姻亲,于阗王族的形象同样作为供养人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这些于阗王族供养像,有名字榜题的有六位,分别是于阗王李圣天和他的妻子曹氏、于阗公主曹延禄姬、以及太子从德兄弟。
对于于阗王族供养像,早期学者们除了利用榜题识读身份之外,主要集中在对几尊没有榜题的供养像的判断上。如李浴最早判断出榆林31窟李圣天夫人的形象,[4]谢稚柳最早完整辨认了榆林31窟的于阗王夫妇供养像,[5]此后学者皆同此说。454窟中的帝王形象在《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即记为于阗王。[6]沙武田在《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中有较为深入的讨论,[7]在文中他总结了前辈学者们的观点,认为98窟、4窟、榆林31窟同为李圣天,454窟则可能是李圣天的儿子尉迟输罗。身份判断之外,学者们利用敦煌文书中的记载,利用图像文史互证,如孙修身在《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8]一文中利用于阗瑞像、于阗王族供养像等探讨了敦煌和于阗的关系。张广达、荣新江整理了大量的与于阗相关的敦煌文书,认为于阗人对敦煌石窟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9]这种敦煌与于阗的交流并非单向,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敦煌对于阗王族的影响。
于阗王像在敦煌石窟中分别出现在4窟、98窟、454窟以及榆林31窟之中。其中4窟、98窟、榆林31窟均为于阗王夫妇供养像,唯有454窟中为一单身帝王的形象。
98窟中的于阗王像(图1),位于东壁门南北向第一身,身形较大,在他身前的牌位状榜题框中有明确标明其身份的榜题:“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李圣天立于华盖之下,头戴冕旒,冕板宽大,上有金轮数枚和二龙戏珠的装饰,六条珠旒,为黑、青相间的珠子串成。冠卷呈筒状,较高,数条龙盘绕其上,玉珠点缀其间,其头侧系有冠带(一说头巾)。李圣天容貌清秀,白面有短须,佩戴耳环,身着黑色衮服,肩部左右绘有金乌与桂树的日月图案,衮服上装饰着四爪龙,下裳为白色,同样绘制着飞翔在山、云之间的四足龙。他右手捻一朵金色花枝,左手持一长柄托板,其上放有香炉,腰间佩有拳头状手柄的宝剑,双足间有一菩萨装地天托足。4窟的位置、形象与之相同,榆林31窟的于阗王位于甬道北壁西向第一身,服饰与之基本相同,只是残损较为严重。

图1 98窟李圣天供养像
李圣天的供养像中的于阗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双足间托足的地天。这一神祇在新疆和田、库车等地的佛教壁画中均有发现,通常出现在佛、毗沙门天王、贵族供养人的双足之间。[10]李圣天的脚下出现地神被认为是因其作为毗沙门天王的胤嗣,在图像上受到毗沙门天王像的影响。[1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和田与库车发现的地天,通常为世俗人物装扮,只是在其头后画出头光,标明其神灵的身份(图2)。但是在敦煌石窟中,毗沙门天王两足间的地神均为菩萨装,如绘制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154窟,南壁西侧的两身毗沙门天王像的双足间,即是一位绾发戴冠、胸装项圈的菩萨。传入汉地之后的毗沙门天王像,足间有地天的,也均为菩萨装。显然李圣天足下的地天,遵循的是汉地图像传统,和于阗本土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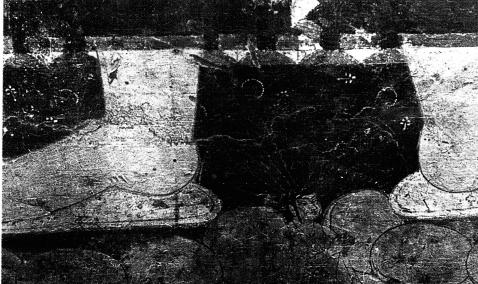
图2 布盖乌于来克遗址坚牢女神像
标明李圣天身份神圣性的地天如此,这位君主的服饰在很多方面体现的也是中原帝王的服饰传统。据《旧唐书》“舆服志”载:
衮冕,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领为升龙,织成为之也。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黻。绣龙、山、火三章,余同上。革带、大带、剑、珮、绶与上同。舄加金饰。[12]
十二旒的规格自唐显庆元年(656)九月开始:
太尉长孙无忌与修礼官等奏曰:准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臣无忌、志宁、敬宗等谨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13]
此后直到宋初,一直延续着十二旒的传统。李圣天的冕旒虽然装饰众多、样式华丽但仍然遵循着这一规格。在李圣天所着的衮服上两肩绘制着日月、衣袖上绘有升龙,下裳绘有山川、云朵、升龙,与唐代的衮服制度部分相合。可见李圣天的装束在一定程度上是秉承汉制的,这同样也表现在454窟于阗王的形象上(图3)。这身于阗王的服饰与98窟中李圣天的装扮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筒状冠卷较为低平,其上装饰着青绿色绘制的玉片。其冕旒同样为十二旒,冕板上绘制着山岳和北斗七星。其身上的衮服同样在肩部绘制着日月,袖口等处绘有四足升龙和凤鸟,其双手合于衣袖之中,足下未见托足的地天。其面部可能是经过后世重新绘制,线条潦草,仍然可以看出其为一长须长者。相比李圣天供养像的细腻精美,此像略显粗糙。但是,其衣冠服饰与《历代帝王图》(图4)中晋武帝司马炎较为相近。《历代帝王图》与敦煌壁画维摩变中的中原帝王形象较为相似,可能是由长安传入的图本所导致。[14]如此,敦煌的维摩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初唐时期的帝王装束样本,此题材在敦煌石窟中经久不衰,虽然每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帝王的服饰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图5)所示,为61窟东壁门南维摩变文殊下方的帝王形象,此帝王所戴的冕旒同样为十二旒,冕板上绘有北斗七星,双肩绘有日月、袖口上为四足升龙的图案,除了下裙为小团花的四方连续图案之外,其服饰与454窟的于阗王非常接近。敦煌石窟中的维摩变,保存了中原帝王的服饰传统,可能成为于阗王服饰的参照。

图3 454窟于阗王像草图(陈粟裕绘)

图4 《历代帝王图》晋武帝

图5 61窟维摩变帝王
对98窟、454窟的于阗王与曹氏归义军时期维摩变帝王形象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于阗王供养像的服饰存在着对维摩变中帝王形象的参照,这在454窟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李圣天的供养像保存了很多个性化的因素,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冕服与维摩变中中原帝王服饰的形制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李圣天之前,于阗诸位君主如尉迟胜、尉迟曜等人虽然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却没有留下关于他们服饰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更久远的高僧惠生与宋云的记载中,看到早期于阗王的形象:
……至于阗国,王头着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15]
从描述上看,这位于阗王的形象颇具特色,与李圣天显然相去甚远。因此,李圣天的汉式的衣冠可能来自于敦煌地区对于早期帝王形象的保留。
二、其他于阗王族供养像
汉式的衣冠服制同样体现在李圣天的夫人,于阗皇后曹氏身上。李圣天的夫人曹氏的供养像在98窟、榆林31窟、61窟、榆林32窟中均有出现。其中98窟榜题为:“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在98窟中同样位于主室东壁门南,立于李圣天身后,身形约是李圣天的一半(如图6)。榆林31窟中位于甬道南壁西向第一身,大小与李圣天一致。榆林32窟中位于北壁西起第一身,与其兄弟曹元深或曹元忠相对。61窟则是位于主室东壁门南侧第三身,立于曹家众多女眷之间。从曹氏在石窟中的位置即可看出其身份的双重性,一方面,她是作为李圣天的配偶出现;另一方面,她是曹议金的女儿,曹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可以脱离李圣天,与其兄弟、姊妹一起立于石窟之中。

图6 98窟于阗皇后曹氏供养像
曹氏的服饰较有特点,在洞窟中其形象稳定,以至于在众多供养人之中非常易于辨认。她头梳双博髻,戴莲花立凤冠,插八柄花钗,其中两柄为步摇,面装花钿,身着黑色交领广袖长袍,内束抹胸,胸饰多层项链,淡黄色的帔帛搭于双臂或绕于胸前,双手于胸前捧香炉或捧盘花。形态端庄、优雅。在其黑色的长袍与帔帛上绘制着缠枝花鸟纹。
这位远嫁于阗的皇后周身装饰着美玉,头冠、耳饰、项链均是玉石镶嵌而成,显示出了于阗的地域特色。但是与曹家另一位异族女眷,头戴桃心冠、身穿翻领窄袖衫的回鹘公主李氏相比,于阗皇后的服饰又展现出明显的汉地特征。曹氏所戴的莲花凤鸟冠为凤冠的一种,在双层莲瓣上站立着一只凤凰,双翅张开,尾巴向后高高卷起。凤冠在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描述石崇奢华生活的一段:
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翔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佩,萦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皇之冠,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恒舞。[16]
凤冠在唐代依然为舞伎所佩戴。天授年间(690-692),武后所造《天授乐》即是“舞四人。画衣五采,凤冠。”[17]此外,晚唐时期,凤冠也为道教中的王母佩戴,宪宗朝(605-802)的著名方士柳泌在一首《玉清行》中,描绘王母的装束:
王母来瑶池,庆云拥琼舆。嵬峨丹凤冠,摇曳紫霞裾。照彻圣姿严,飘飖神步徐。[18]
凤冠出现礼仪、等级的分化从《旧唐书》与《宋史》“舆服志”中记录皇后的礼服中看出端倪:
《武德令》:皇后服有袆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其衣以深青织成为之,文为翚翟之形。素质,五色,十二等。[19]
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寇饰以九龙、四凤。祎之衣,深青织成,翟文赤质,五色十二等。青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襈,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20]
两条文献对比,可见唐、宋皇后服的一个显著不同是九龙四凤冠的运用。这种头冠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皇后像,如《宋仁宗皇后像》(图7)画面中的皇后曹氏头戴金属质地的覆钵形头冠,其上镂空雕刻着龙与凤凰,冠后插有双翅,头冠上镶嵌着大量珍珠与宝石,华美异常。五代时期的皇后服饰虽无明确的记载,而在唐、宋之间,皇后服饰出现了一次较大的变化:凤冠成为皇后身份的象征,不再像以往那样女子皆可使用。

图7 宋仁宗皇后像
再回到敦煌石窟之中。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所绘制的曹家女眷们的供养像基本上是千人一面,唯一不同的是头饰上的花钗数量所象征的等级,如在61窟中站于于阗皇后身后的“广平郡君太夫人宋氏”佩戴有十二枚花钗(图8),其旁的出适翟氏的“谯县夫人”佩戴十枚花钗。因此可以看出曹家所恪守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于阗皇后曹氏所佩戴的莲花立凤冠当是其皇后身份的象征。头冠之外,衣裙、帔帛上的缠枝鸟纹,鸟身纤细,尾羽修长,可能即是文献当中记载的“翟文”。因此,于阗皇后的服饰所遵从的礼仪规格当是来自中原的皇后礼服。

图8 61窟曹氏家族女供养人像
于阗公主李氏的供养像也体现出汉地礼服的特征。李氏原为李圣天的第三女,在敦煌石窟之中是作为曹延禄的配偶出现,称为曹延禄姬。其供养像在61窟之中位于东壁门北侧第七身(图9),立于曹家女眷之间。榜题为“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此外还有202窟西龛北侧南向第一身榜题为“大朝大于阗国公主……李氏供养”,榆林25窟前室甬道北壁一身,榜题为“大朝大于阗金玉国皇帝的子天公(主)”。曹延禄姬的服饰与于阗皇后曹氏的服饰基本一致,只是发间所戴的花钗数量为四枚,其中两枚为步摇,从中可见两者之间的等级差异。

图9 61窟曹延禄姬供养像
据此服饰特点,笔者2011年秋在莫高窟考察时发现12窟甬道北侧一身女供养人像与之相同,虽无榜题,但其明显、独特的服饰特点亦能证明其身份当为曹延禄姬。石窟中的供养像之外,在敦煌藏经洞中亦有一幅与其相关的绢画,据王国维先生所记南林蒋氏藏绢画《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之盛装女子画像题记“故大朝大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21]这幅作品高106厘米、宽58厘米,今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馆藏编号为35.11号。从其编号来看当是1935年收购所得。此幅绢画发表极少,画面上部为半跏趺坐的披帽地藏,左手托宝珠,右手外伸,右侧卧着金毛狮子,其上为道明和尚,左侧为持锡杖的五道将军,两者均有榜题。画面下半部中间的榜题框大半空白,左侧绘有一身跏趺坐的菩萨,右侧为身着红衣的于阗公主李氏,她头戴凤冠,跪地踞坐,双手持长柄香炉,身后有二举着团扇的侍者。据载:咸平五年(1002)“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发生政变,“曹延禄等知其力屈,寻自尽”。[22]曹延禄姬可能亦随其夫而去,这幅地藏菩萨像可能为其追荐之作。此图中除去衣衫颜色,其余服饰与洞窟中的供养像一致。可以看到,曹延禄姬的礼服装束是比较固定的。
礼服之外,于阗王族身着的常服也为汉式。如于阗太子从德的供养像。此像位于244窟甬道北侧。西起第二身供养像下方有一小像,为一双手于胸前持一长杆状物的男童,其身侧榜题为“德従子□德太子”与其相对的南侧西起第二身供养像下方亦有一身装束相同的男孩,榜题为“戊□□五月十□日□□太子”可能为从德的兄弟。兄弟二人皆是着白色圆领窄袖衫,头侧梳双髻,余发披于肩头,为典型的汉地男童装扮。
这些于阗王族在服饰上与于阗本土的供养人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和田巴拉瓦斯特遗址出土的一幅供养人壁画,画面中的一家三口正双膝跪地,做礼佛状,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6世纪时于阗本地人的服饰特点:男子身着窄袖长袍,束着腰带;女子穿翻领束腰长袍,喇叭式宽袖口,下身着长裙;儿童着中长的圆领窄袖袍。与之相似的装扮也出现在丹丹乌里克遗址CD10西北墙、西回廊下方的壁画上,半袖或长袖的圆领窄袖袍为其主要的服饰。与这些本土的中、下层供养人相比,李圣天等王族已经通过与沙州政权的接触,出现了汉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光体现在服饰上,在他们参与的敦煌佛事活动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于阗人在敦煌的佛事活动
在敦煌文书的记录中,于阗人在敦煌参与的佛事活动[23]主要有四项。
(1)写经。包括于阗文和汉文,如P.3510于阗文文书,其中一件为《从德太子发愿文》,[24]末尾于阗文题:“从德太子一切恭敬,敬礼佛法,命人写讫。”P.3148V题名:“甲子年八月七日,于阗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内,将《法华经》第四卷。”龙谷大学藏第48号《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题记:“于阗册礼般若先排使张宗瀚留此残本”。
(2)施舍供养。主要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参与供养。如P.3111《庚申年七月十五日于阗公主官造施舍纸布花树及台子簿》,即为于阗公主在盂兰盆节用纸布花树供佛。
(3)补绘壁画以及开造石窟。在补绘壁画方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444窟东壁门上方于阗太子从连与琮原补绘的《法华经·见宝塔品》。444窟为曹氏归义军时期补绘的洞窟,其西龛内、南北两壁的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为盛唐时所绘,曹氏归义军时补绘了洞窟,并且缩小了甬道口。于阗太子从连与琮补绘的《见宝塔品》位于东壁,为一圆形佛塔,塔座较高,没有绘制塔刹,纵切面为“m”形,释迦、多宝佛均结跏趺坐,坐于宝塔中的束腰莲台上。释迦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竖于胸前,其旁的塔身上墨书“南无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花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多宝佛着衽右式袈裟,左手握袈裟一角,右手置于腹前,似在指物,其旁的塔身上有“南无多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的题记。虽然有明确的题记表示它与于阗皇太子的关系,但是释迦、多宝佛的身形、服饰、设色等方面与敦煌石窟中同一时期的其他佛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可能两位皇太子只是对其进行了重装,并没有改变它原本的样式。
(4)于阗人在敦煌还有开窟的活动,如《于阗天寿二年九月弱婢佑定等牒》[Dx.2148(2)+Dx.6069(1)]中记载了婢女佑定向曹氏与宰相索要物品,以备开窟之用。明确记载的以于阗人为功德主的洞窟有位于莫高窟北侧山顶上的土塔“天王堂”,塔内东壁有功德题记残留。题记中可以辨识的内容并不多,但是已经明确指出此塔的功德主为曹延禄与曹延禄姬。塔中遍布着以观音曼荼罗为主的密教题材绘画,画面中的菩萨多为头戴山字形头冠,波浪状卷发披拂肩头,带马蹄形彩虹条纹头冠,珠链穿缀而成的禅思带绕臂。
另一个使用这种样式并由于阗人供养的菩萨是一座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小型六面木塔(图10)。塔上分上下两层,绘制着手持各种法器的菩萨,他们的样式与天王堂中的菩萨相一致。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对其记录如下:
又见一木塔,六面俱绘佛像,彩色如新,描绘极精,不失五代宋初规模。木塔中空,据说明书云,内中原有小银塔一,银塔上镌“于阗国王大帅从德”云云。原出敦煌千佛洞,今银塔为马步青攫去,而以木塔存武威民众教育馆。五代时于阗与瓜沙曹氏互为婚姻,则此当是于阗国供养千佛洞之物。银塔所镌铭文虽未窥其全,然其有裨于瓜沙曹氏与于阗关系之研究则无疑也。[25]

图10 于阗彩绘木塔
这一木塔中所记的“于阗国王大帅从德”可能即是244窟的“太子德从”。即是李圣天与曹氏的长子,从德太子。他可能在敦煌长期生活过,967年回于阗继承王位[26]这座木塔菩萨的排列组合带有很强的密教色彩,曹延禄姬与其兄长从德太子都选择了这一样式的菩萨可能不是偶然。虽然在于阗本土尚未有这种样式的菩萨发现,但是这其中反映了于阗王族对于密教的信仰。长期以来对于于阗的密教图像一直存在着争论,于阗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出土的千手千眼观音是于阗密教流行的一个证据,曹延禄姬为功德主的“天王堂”与从德太子的彩绘木雕佛塔亦能反映出这方面的状况。
于阗本土只有佛寺发现,并没有石窟,于阗人参与开窟活动,可能是受到敦煌习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德可能为其父李圣天开窟了“天子窟”。这一记载见于敦煌文书P.3713v:“七月廿六日,粟一斗,东窟上迎大太子看天子窟地用。”[27]据沙武田考证,这一记载中的东窟为榆林窟,大太子为从德太子,并根据于阗王夫妇供养像等图像将“天子窟”定为榆林31窟。
确实,在榆林31窟中出现了李圣天夫妇供养像、天王像等具有明显于阗特征的图像。而与之毗邻的32、33窟中同样有于阗皇后供养像、新样文殊、位于牛头山中的普贤并侍从图、通壁佛教圣迹图等具有于阗特色的图像。因此可能这三个洞窟在图像的选择与使用上存在着特殊的偏好。
但是除了榆林31、32、33窟相对集中之外,敦煌石窟中具有于阗因素的图像散见于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所修建的洞窟之中。榆林31、32、33窟在石窟空间的安排与布局上和曹氏归义军时期所开造的敦煌洞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在敦煌存在的于阗因素已经被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敦煌民众所吸收,从而这些图像在汉族民众开造的洞窟中也有大量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在敦煌石窟中无法在图像上将于阗人所开造的洞窟从汉族洞窟中区分出来的原因。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于阗人在敦煌参与的佛事活动与本地汉族民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些与敦煌关系密切的于阗王族,在信仰方式上也与汉地相同。不同于早期汉地僧侣前往于阗求法,敦煌本地代表的汉地佛教,对于阗王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深重。
这种通过佛教产生的影响甚至绵延到于阗本土,1983-1984年,和田布扎克乡依玛木·木沙·卡孜木麻扎发现一处五代-宋初的墓葬群,现称布扎克墓地。这里出土一批彩色木棺,其中三座开棺整理,木棺为前高后低式,其上绘制有彩色图案。其中一件男尸头侧随葬一件白绫,一面墨书于阗文,一面书汉文:“夫人信附男宰相李旺儿。”[28]因而可知此处墓地规格很高,可能为于阗王族的家族墓地。现藏于和田博物馆的一具为船形,上下两层,上部棺盖上有木制圆钉覆盖,头档及左右两侧绘制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案(图11)。头档板上为一朱色大门,其上站立着一只正面朱雀,两侧为飞腾状的青龙、白虎,青龙四足,后档为龟蛇缠绕的玄武。其下有带栏杆的台相承,台四周绘制有壼门,中间绘对鸟纹。有学者指出,这种棺木的形制模仿的是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舍利棺,[29]并且其四周四神的配置在山西太原龙泉寺地宫中的舍利棺上亦有发现。[30]由汉式的舍利棺的形制发展而来的于阗王族丧葬棺,体现了这些晚期的于阗王族们从汉地学习、吸收佛法、艺术的倾向。

图11 布扎克墓地彩绘木棺
小结
于阗王族在敦煌活动的痕迹通过洞窟壁画与文书保存了下来,这些珍贵的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正史记载之外的于阗,呈现出了晚期于阗王族的汉化倾向。一方面是衣冠服饰秉承汉制,一方面是他们所进行的抄经、开窟等佛事活动与敦煌民众趋于一致。于阗王族、上层贵族显然对敦煌、汉地颇为了解,他们与敦煌的交流,使汉文化、汉地佛教向西回流。在促进于阗本土贵族的汉化这一点上,远嫁于阗的曹议金之女及可能在敦煌长期居住过的从德太子或许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注释:
[1]吐蕃占领于阗的时间,暂以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安迪尔古城发现的贞元七年(791)题记为参考。参见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2][12][13]《旧唐书》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五”。
[3]吐蕃在其占领区中推行的易服政策,从敦煌莫高窟中吐蕃占领时期的大量吐蕃装供养人像中可见一斑,另敦煌文书P.4638(3)、P.4640(1)《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中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纹)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的记载。近年在对新疆和田的考古发掘中,也有疑为吐蕃装人物壁画残片的发现。
[4]李浴:《榆林窟佛教艺术内容调查》,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藏,此处转引自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注释3。
[5]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6]《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68页。
[7]参见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8]孙修身:《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9]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敦煌文书P.3510〈从德太子发愿文〉及其年代》《关于敦煌出土的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10世纪于阗国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等论文,收录于《于阗史丛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此图像见于克孜尔尕哈13、14窟中,参见彭杰《于阗的地神崇拜及其图像的流变》,收录于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51-260页。
[11]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
[14]参见王中旭《敦煌翟通窟〈维摩变〉之贞观新样研究》,《艺术史研究》2012年第14期。
[15]《洛阳伽蓝记译注》,卷五“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16]《拾遗记》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第215页。
[17]《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
[18]《全唐诗》五百零五卷,中华书局,1999年,第5745页。
[19]《旧唐书》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五”,“舆服”。
[20]《宋史》卷一百五十一,“志第一百四”“舆服三”。
[21]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999页。
[22][清]徐松辑:《宋会要集稿》,中华书局,1957年,第7767页。
[23]关于敦煌文书中于阗人的活动情况,张广达、荣新江在《关于敦煌出土的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中有细致讨论。收录于《于阗史丛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105页。
[24]张广达、荣新江:《敦煌文书P.3510〈从德太子发愿文〉及其年代》,《于阗史丛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页。
[2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1页。
[26]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收录《于阗史丛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0-81页。
[27]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28]姚书文:《新疆和田布扎克墓地出土一号彩色木棺的加固保护》,《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合刊。
[29]吴艳春:《从和田布扎克彩棺看唐-五代长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30]参见《山西太原唐佛塔地宫出土五重棺椁》,2008年11月28日《中国文物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
(来源:《美术研究》2014年第3期,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集[1964-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