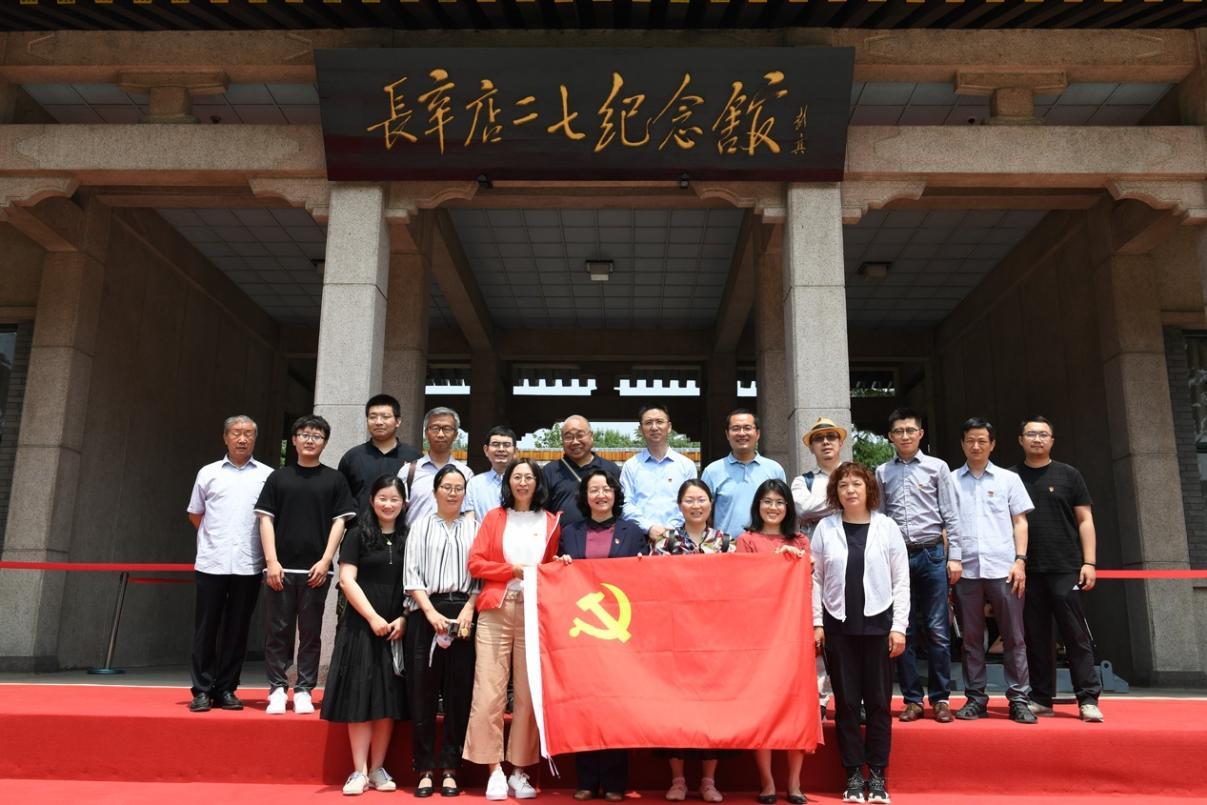摘要:方以智的生死哲学是晚节的内在支撑,其代表性观点是生死为正余关系,生与死如同春夏秋与冬,且可相互轮转。由生出发,经过无生(死亡)的超越,再返回尽此生。国破家亡后,方以智历诸患难、久经生死考验,逐渐由被动承受转为积极担当,并将这些经历与考验转化为打开儒学死亡视域与锤炼生生仁体的资源。方以智将佛教能医治诸病的药树思想引入儒学,其形成及发展有梧州、南京、新城三个阶段,其代表性观点分别为:引西方药树为奇兵(以佛援儒)、死是大恩人(以佛教的超越精神解决生死问题)、病药俱忘还说药(重返儒学之着实)。方以智晚年驻锡青原山,荆(佛)杏(儒)双修,伏藏隐忍,在明亡的寒冬中“炼药开炉(冬雷破雪)”,以余求正,启动生死转化的生生之几,并淬砺为中国文化托孤之志,这可视为药树思想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方以智药树思想的哲学特色是“应病予药”,其要点有:承认病与药的普遍性;根据病症,辩证用药,善用奇药;擅长运用作为三教共同基础的公因之药,以及公因与反因的轮转。方以智以疗教救学为使命:通过佛道为儒学寻找应对危机的方案;佛道亦可借鉴吸收儒学尊生的入世精神,推动世俗化进程,由此实现“三教互救”基础上的三教合一。
关键词:方以智;药树;生死;三教互救;应病予药
作者:张昭炜,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方以智的哲学精神”(项目编号:21FZXB021)的阶段性成果。
与佛教、道教不同,儒学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宗教团体、宗门领袖,而是在个体修身、家庭伦常、国家政治表现其思想,重在着实的入世之教,以尊生为主;佛道主超越的出世之学,重视死。由于儒学占据明代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即使明儒倡导三教合一,其本质多是以儒学统佛道,如王阳明以三间喻三教,三间共为一厅,儒者割左右间与之佛道。[1]随着明代的国家政权灭亡,儒学的入世之学难以展开,清廷大肆杀戮,却默许佛道,在此情况下,有气节、有担当的明代遗民饮吞亡国之恨,栖身佛道之门,并借机吸取佛道超越死亡的出世之学,以充实儒学,方以智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王阳明之后,明代宗教学发展有“三教独立”与“三教合一”两种主要趋势:前者代表有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方以智曾祖方学渐、祖父方大镇与东林之学相符,独尊儒学;后者代表有林兆恩、焦竑等,方以智的外祖吴应宾与林兆恩、焦竑之学相合,并汇聚憨山德清、紫柏真可、云栖祩宏三高僧之学。两种趋势通过方吴两家的联姻实现汇聚,这是方以智创新发展三教思想的先天有利条件。无论是“三教独立”还是“三教合一”,其中隐含的前提是将儒学视作宗教,体现出宗教的性质:“相信自然与人类生命的过程乃为一超人的力量所指导与控制的,并且这种超人的力量是可被邀宠或抚慰的。”[2]宗教须具备抚慰死亡的终极关怀。死亡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事件,佛教涅槃,道教养生,都是力图给出死亡问题的解决方案。儒学相对缺乏这一面向,倾向于消解超人的力量,其代表性论述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与此相应,儒学的核心概念为生生之“仁”,宋明理学家主要从生的角度诠释仁体,如以核仁喻仁、以觉言仁等。在此基础上,儒学亦有宗教的拓展,“儒家思想有一超越的面向”,“儒家的现世观具有深远的宗教性。”[3]宋明理学家亦有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指向。[4]如果将儒学视作宗教,须打开死亡的视域;更进一步,以死亡视域促进生生之仁,锤炼生生仁体,这依赖综合创新的大思想家。
在方以智研究中,自从余英时出版《方以智晚节考》以来,晚节成为方以智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不仅关乎方以智思想的归结、方以智作为“明代文天祥”的定位,而且关乎整个宋明理学的学脉。余英时主要通过史料的考辨论证方以智的晚节,在此基础上,还可进一步考察方以智的思想发展,由内在精神支撑、生死哲学佐证,进而内外一致,更有利于方以智晚节研究。[5]据方以智的重要哲学著作《易余》卷上、下首句:“欲疗教而平人心”[6];“九死之骨,欲平疗教者之心,心苦矣!”[7]“疗教”之“教”当指儒学,如“烹雪炮漆,以供鼎薪,偏教医活死麒麟。”[8]以佛(雪,雪山)道(漆,漆园吏)为药,医救儒学(麒麟)之病,这既是方以智学术思想的指向,亦是方以智哲学宗教思想的方法论,两者均以“药树”为基础,体现出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统一。“鼎薪炮庄,苦心如此,供养后世,谁得而知之。”[9]由此昭示了方以智气节的内在基础、深沉追求、使命与担当,他的学术视野不限于明清之际,而是指向未来,致力于指引中国宗教的总体发展方向。
一、药树思想的三个阶段
据桐城同乡、姻亲孙晋记述方以智思想的发展:
曩闻苍梧句曰:“西方药树是奇兵。”已闻竹关句曰:“死是大恩人。”已闻廪山句曰:“病药俱忘还说药,医王大病欲谁医?”[10]
按此而论,方以智的药树思想包括苍梧(梧州云盖寺,1651-1652年)、竹关(南京高座寺,1653-1655年)、廪山(新城廪山寺,1659-1662年)三个阶段,分述如下:
1.引佛教之奇兵救儒学
方以智是明朝的孝子忠臣,其生死考验与明亡紧密相联。他亲历崇祯、弘光、永历三个政权:崇祯吊死,众臣惟恐避之不及,而他恸哭崇祯灵位于东华门,为李自成军队所执,几折磨近死;方以智与陈子龙、冒辟疆、侯方域等相与推重,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在南京,遭仇家阮大铖追杀;流离湖广,他参与永历政权,永历举朝“如醉如梦,妄相妄忆而已”,“曾见有几而作不俟终日者三人,吴璟、方以智、毛毓祥也。”“方以智参机密,见涣发丝纶不达城外,托修道而入山。”“当时国势危如累卵,清势重若泰山,而举朝文武犹尔梦梦,欲不亡得乎?”[11]面对危机,永历君臣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沉迷醉梦,逃避现实,粉饰太平。“涣发丝纶不达城外”,政令不能下行,民意亦不能上达,已成亡国之势。在此情况下,方以智不得已退隐山林,“同伴都分手,麻鞵独入林。一年三变姓,十字九椎心。听惯干戈信,愁因风雨深。死生容易事,所痛为知音。”[12]方以智身在山林,心系庙堂,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久经患难后,他对死生渐趋淡然,所系念者,惟有知音而已。永历三年(1649年),“进方以智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召入直,称疾不赴。”[13]桂林沦陷,兵部尚书瞿式耜、总督张同敞等知音悲壮而死,对于方以智而言,可谓是痛上加痛;为救友人,方以智直赴刑场,“狮子尊者肯施头”[14],“一声狮子吼,刀锯总忘机。”[15]方以智通过佛教涅槃精神超越肉体的死亡,这表明他此时不仅熟知佛教典故,而且能用于解决生死问题,这表明他对佛教的综合理解与深入体证。综观这一过程,方以智忠君爱国,即使在仕途受阻后,亦未完全退隐山林;当有志气、有担当的知音纷纷陨落后,方以智毅然挺立,直面死亡的威胁,体现出超越生死的气质。据永历五年(1651)方以智作自祭文:“一齁元会太分明,生即无生尽此生。中土杏花知正命,雪山药树用奇兵。便将鼎镬烹真乳,仍以刀锋扫化城。”[16]孔子讲学杏坛,“杏花”代指儒学;“药树”出自佛教,“《善信经》云:有神药树,名曰摩罗陀衹,主厌天下万毒,不得妄行。”[17]药树能祛除万毒,又名药树王,佛教信众亦有化身药树之愿:“愿作药树王,遍覆众生界;见闻及服药,除病消众毒。”[18]“西方药树是奇兵”又作“雪山药树用奇兵”,雪山与西方指佛教,“为世间之钩琐苦不得出,故示雪山以立此脱离之极”[19],“脱离之极”相当于佛教超越生死的“无生”。面对鼎镬,方以智引入“西方药树”,诉诸于佛教超越生死的思想资源,这可呼应《易余》的“自为药树”[20]。“奇兵”思想当据《道德经》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由此抽象出“正”与“奇”两个对待概念:正为常用之法,奇为偶施之教。天下太平,正显而奇隐,儒学在生生开显之域,如同治国以正而罕用兵;国家危亡,修齐治平之正用受阻,方诉诸于奇兵,以补足儒学之仁的“无生(死亡)”视域,此时奇显正隐。正奇思想可呼应孔子的“未知生”之论,常态时知生即可,用正兵之常,不必引入死亡之奇兵。
第一阶段主要化解死亡的威胁。由正奇发展出正余关系,“正”是常态的显性维度,“余”则是偶态的缄默维度。“生即无生尽此生”包含两阶正余关系:第一阶,生与死为正余关系,“正”如同春夏秋三时,是生生的绽放;“余”如同冬,是无生的沉寂。通过“生即无生”,实现正余互通,由“生”超越至“无生”,无惧死亡。“生即无生之乘,正居南午藏子之位。”[21]如同显南而藏北、显午而藏子,正余的表现形式通常是显正而隐余,由此可以解释孔子常言生,而罕言死,是因为言“正”而“余”在其中。第二阶,“无生”与“尽此生”亦为正余。这阶关系表现为超越“无生”后,再返回“尽此生”,相当于以余返正。[22]两阶关系综括了佛教的出世超越与儒学的入世尊生,置于死地的“鼎镬”转为“烹真乳”。以死炼生,刀兵劫有助于扫除常见妄见,以超越至真实的“无生”,并返回“尽此生”。经此诠释,刀兵劫不再是被动的消极义之杀戮,而是成为获得超越并返回着实的资源。“吾家尼麓水,今日浴曹溪。”“跳出乾坤外,能投汤火中。”[23]从现实的表现形式来看,方以智偏离了正统儒学的家学传承,转向佛教(曹溪代指六祖惠能、禅宗)。由第二阶正余关系可知,佛教仅是手段,方以智通过汲取佛教的超越精神(“跳出乾坤外”,相当于“无生”),在自祭中实现重生,重返儒学之正(“能投汤火中”,相当于“尽此生”)。综上,方以智以儒学为起点,亦以儒学为归宿,始终以儒学为主;佛教之奇兵为中间阶段,可视作手段,以此打开儒学超越生死的视域,用于化解死亡威胁。
2.死是大恩人
第二阶段正面阐发死亡的重要意义。逃离岭南后,方以智遭遇皖江抚军之难,“癸巳春,复因归省,两遇煴火,业缘难避,安于所伤已耳。”“煴火重煎髑髅髓,家常炉炭寒冰洗。涅槃堂中弹一指,指端吼出五狮子。”[24]经广西之难后,方以智对待皖江之难的态度较为平和,“安于所伤”,淡然处之;禅宗思想对于方以智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以涅槃精神化解、超越死亡的威胁,将苦难作为锻炼肉体、成就道身的资源。为避难,方以智拜入觉浪道盛门下,至南京高座寺的竹关闭关,得闻“死是大恩人”。第一阶段的死亡威胁源于外部,方以智被动去承受;第二阶段转为方以智感恩死难的经历,“吾不罹九死,几负一生。”[25]生命因“九死”而丰富饱满,方以智由对死的被动承受转向主动担当,由消极转为积极,“以生死来处发药”[26]。在拜入觉浪道盛之前,方以智的药树思想已然经过第一阶段,觉浪道盛指点与方以智内证合拍(外缘与内因相印):“生于忧患,置之死地而后生,杖人曰:‘贫病死是三大恩人。’”[27]生死为正余,以余求正,由死求生,故言死是大恩人,亦如觉浪道盛以“一茎药草”能活人。贫病死是宗教产生的根源,然而,这三者可作为药,医救世俗着实之教,激活生生之仁。“死是大恩人”可呼应吴应宾的教诲:“每闻先外祖‘雪里打春雷,中有大父母’,后从刀兵水火中,息喘杖人之门,又闻‘死是大恩人,乃祝无量寿’。由今看来,以雪埋雷,以死祝寿,不妨奇特。有触此语,彻底放下,得一场大庆快者么?果然绝后重苏,通身白汗。回视一切利害得失、人我生死,瓦解冰消,由我自在出入香水海中。”[28]生与死为对待,“瓦解冰消”是消除对待之后的绝待,自在出入生死。寿是生的延续,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其对立面之“死”,以余求正,故言以死实现无量寿。吴应宾的教诲早于觉浪道盛,[29]对应“由死求生”的关系如下:

“雪里打春雷(以雪埋雷)”即是以死求生、以死藏生,包含两层关系:(一)雪代指冬,是“余”的缄默;春雷代指春,是“正”的显化。以雪埋雷指向“以余求正”的“冬炼三时”。(二)雪代指静,雷代表真动生生,此是“静极而真动”[30]。上述隐义在《药树堂铭》“冬雷破雪”有展开,指向生生之几,将在下文论述。结合第一阶段的奇兵思想,再引入类似的概念:奇与庸。庸为常用,庸奇的关系相当于正奇、正余。“以奇金刚杵,化庸火宅;以庸甘露瓶,成奇香水海,是曰奇教,是曰庸宗”[31]。由此指出了引佛入儒的重要意义:西方药树之“奇”是“金刚杵”,佛教以此法器实现儒学尊生的转化与超越,故为奇教,为药;同理,中土杏花之“正(庸)”是“甘露瓶”,儒学以此法器遍洒入世,泽被苍生,成就功德洋溢的香水海,故为庸宗,亦为药。以上表现出儒学与佛教互通互证、互为病药的大宗教观。
第二阶段的焦点仍是死,高座寺闭关继续解决生死问题。从病药互用来看,“杖人曰:‘知佛祖之特以生死二字,为人着力处乎?舍此亦无从施设法药矣。’”[32]“惟有‘生死’二字,是世出世间逃不得底,故用以发药。”[33]生死发药的现实意义便是实现“绝后重苏”,如雪中待春雷。死的意义与死后归宿是宗教的终极问题,如前所述,从孔子创说开始,儒学主要在生的场域展开,死是儒学试图悬搁回避的问题,乃至成为其短板。佛教则不然,“佛以生死发药,按析解剥,为此土之所不及察。”[34]佛教深知生死问题是“世出世间逃不得底”,故重视死亡视域的打开,以及死对于医救生的药效,这是方以智从佛教吸取的重要思想资源。如果盛世太平,方以智仕途顺达,践行儒学纲常伦理,也许不会直面死的考验、深度思考死的意义,而正是国破家亡、万死千难的经历,使得他不得不去正视死。在这一过程中,方以智受益于吴应宾与觉浪道盛的生死观,并感恩磨难的经历,故言“死是大恩人”,“死死者不死,以死知其生。”[35]在生的场域关闭后,通过求助于死之“大恩人”,将死作为实现生的手段,借助死之“余”实现生之“正”,以死证得不死,从死中磨砺出生机焕发。
3.病药俱忘还说药
第三阶段是方以智主持新城廪山寺时,超越病与药(病药俱忘),这既显示出方以智医术纯熟后,超越病与药的名相,追求大医王的境界。[36]这一阶段还可先前推,“印心杖门,于栾庐时,得药地图章,因随所在,名为药地愚者。呜呼!本无病药,在药病中,舍身为药树,其愚不可及也。”[37]“本无病药”可与“病药俱忘”相应,亦可说是“生死俱忘”,三者均具有消除性,倾向于“无相”的超越,但又不像《金刚经》《坛经》那样追求“无相”,而是“还说药”,从“无相”再返回到“有相”。药地与药树在此同时出现:从相通处来看,两者都以药为出发点,意在治病;从差异性而言,药树重在能治诸病,疗效神奇;药地侧重作为动词宾语的“地”,要救治天地群生,境界高远。参照“余”论,地天互余,[38]“药地”亦是“药天”,合称“药天地”,方以智要做“炮地蒸天古药杵”[39],医救天地群生。药地与愚者并称,愚如移山之愚公,知其难为而为之,方以智舍身为药树,愿力宏大,融合了佛教的大愿精神,医救天地群生。
返观药树思想的第一个阶段,“生即无生尽此生”显示出方以智的药树思想是以儒学“尽此生”为指向。第三阶段“病药俱忘还说药”依然是以儒学为旨归,生与死对应着实与超越。以儒学着实为起点,“病药俱忘”是超越着实,“还说药”是从超越返回着实,即“再着实”。综合三个步骤:着实—超越—再着实。这三个步骤各有其用,从着实到超越,可理解为儒学吸收佛教的超越精神;从超越到再着实,可理解为将佛教的超越精神灌注到儒学。经过三个步骤,儒佛均尽其极,并在融合中俱得提进:以佛教超越之药医治儒学着实之病,儒学着实之药亦可医治佛教超越之病,如佛教可能导致空观、出世等风险,通过儒学的再着实来防范风险。超越与再着实的进路便是《易余》的点睛之笔:“矐肉眼而开醯眼,又矐醯眼而还双眼者,许读此书。”[40]“醯眼”为慧眼,相当于超越,“肉眼”相当于世俗的着实,由此包括两个进路:由着实而超越,再由超越返归着实。开慧眼是打开宗教死亡的视域;通过“还肉眼”,将此转作用于世俗的生生,从而实现儒教的人文化与世俗化。以上所示的关系基本遵循了从起点之“正”出发,经过中间之“余”,再返回起点之“正”,也就是轮转,在方以智哲学中也可称之为“翻车”,或者说是三反:“生死反乎死生,有生死反乎无生死,无生死反乎善生即善死,此三反也。”“反者,翻也。”[41]“翻”即是轮转,三反的内在哲学基础是正余的互换轮转:第一反是在生死之间,着实内部的翻转;第二反是生死与无生死之间,着实与超越的翻转;第三反是无生死与善生善死之间,重返着实。从起点来看,遵循孔子的传统,儒学的死亡视域处于关闭状态,也可说是贫乏之极。经过方以智的三反轮转,儒学的死亡视域不仅打开,而且借助佛道,实现了丰富的扩充,达到了与佛道同等的理论高度,甚至在返回着实方面,儒学更胜一筹,这显示出方以智的宗教观对于中国儒学宗教化进程的提进与奠基性的理论贡献。
4.庄学思想的协同发展
“雪山药树用奇兵”是烹雪(佛教)为药,引佛救儒;“烹雪炮漆”,亦可炮漆(庄学)为药,将庄学作为医救儒学的“奇兵”:“《庄子》,奇兵也。”[42]在第一阶段引入西方药树时,方以智亦将庄子引入,如其自祭文:“蒙庄氏日以齐生死、一殀寿为言,而乃哼哼于曳尾、栎社树养生全其天,若真有莫可奈何然者,夫乌知剖心纳肝之为大养生乎?”[43]庄子解决生死问题的方案是“齐生死”(如《庄子·齐物论》“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是方以智超越生死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中内在的哲学基础便是“生死正余”:正与余相反相因,相因通过“齐生死”实现,“纵横杀活,隐显正奇”[44],呼应“西方药树是奇兵”。庄子的追求如楚之神龟的闲逸,“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栎社树“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庄子·人间世》),在方以智看来,“齐生死”寓居有“剖心纳肝”之死,这已透露出类似于托孤说的使命感,并以此成就“大养生”,激发出第二阶段的“死是大恩人”。“庄子正以虚无为反对之药,而归实于极物耳。”[45]传统的庄学形象表现为虚无、旷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与之相对的儒学着实、曲谨,庄学与儒学为相反对立的关系。方以智炮庄为药,即是通过相反相因的“正”“余”转化,以庄子的虚无、旷达去激活儒学,[46]使得儒学融合虚无、旷达的精神,并能“再着实”,由此亦可呼应“病药俱忘还说药”以及三眼喻。庄子思想内部亦有着实的进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方以智的诠释相当于发展了这一进路。
从明代庄学思想发展来看,王阳明的弟子朱得之引老庄之学入阳明学,焦竑、公安三袁等阳明后学亦有推进。吴应宾与焦竑、公安三袁唱和,从而有利于接受以儒解庄的进路;憨山德清是明代以佛解庄的重要代表,吴应宾师承憨山德清,在继承儒佛解庄的基础上,吴应宾集成创新,据马其昶曰:“予读《宗一圣论》,缘圣以为一,缘一以为宗,其殆拟漆园氏之所为邪?”[47]吴应宾在其代表作《宗一圣论》中熟练运用庄学思想,这深刻影响了方以智《易余》《东西均》《药地炮庄》的创作。吴应宾集成了当时一流的庄学思想资源,并传授给方以智,这使得方以智的庄学思想天然具有三教融合的背景。方氏家传以儒学为宗,吴应宾为方以智暗植佛庄,从而有利于方以智面对广西、皖江之难。吴应宾与觉浪道盛相识相知,亦有利于方以智拜师觉浪道盛,接受炮庄之托,由此促成了觉浪道盛与方以智以庄托孤的因缘。“药树”思想与庄学相会相合,烹雪炮漆以救儒,成就了《药地炮庄》。据潭阳大集堂本《药地炮庄》牌记:“天界觉大师评,吴观我先生正。”[48]由此亦可印证吴应宾与觉浪道盛的庄学思想是《药地炮庄》的两大来源。
综上,药树思想的三个阶段依次递进,相互印证:在第一阶段引入药树奇兵时,据方以智自祭文,“能以死知其所以不死,知不死之无不可以死,则此死也,诚天地之大恩矣。”[49]第二阶段“死是大恩人”亦随之而至,因此,第一阶段可以包含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土杏花知正命,雪山药树用奇兵”指向儒佛互用,这延续到第二阶段,觉浪道盛认为:“杏花药树,真空妙有。以貌例之,无不反判。果知其故,皆一贯也。”[50]这涉及到方以智以佛教(药树)为药,救治儒学(杏花)之病,即是“西方药树是奇兵”,亦可由此对接荆杏双修,将在下文论述。第一阶段引入佛教药树医救儒学,药树思想的义理尚未融彻。觉浪道盛视杏花(儒)与药树(佛)为反判,通过相反相因,儒佛一贯,由此促成了第二阶段,并在义理层次解决了方以智抉择儒佛的难题。觉浪道盛的“反判”相当于方以智的“反因”,正与余(奇)为反因。如同良医诊断,明晰患者得病之故,方能对症下药、正奇互用,达到良好的疗效。“真空妙有”可对应超越着实,第二阶段重在引入佛教超越的精神,如同真空;第三阶段则是由真空返回妙有,回归儒学的着实。综上,第二与第三阶段构成反因。相反者相因(对立统一),相因的结果是通过佛教的避路,方以智曲折实现了儒学的归路。
二、药树思想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炼药开炉
方以智晚年主持吉安青原山净居寺(1664-1671年),继续发展“病药俱忘还说药”,重视药的利用及展开,“炼药开炉(冬雷破雪)”可作为药树思想的第四个阶段。禅宗七祖行思开创青原道场,下衍曹洞、云门、法眼诸宗,觉浪道盛属于曹洞宗法系,方以智主持青原,相当于回归祖庭。青原山具有儒佛双修的深厚文化底蕴。阳明学是明代儒学的显学,江右王门是阳明学的中流砥柱,青原山是江右王门的中心,时称“西江杏坛”[51],“弦诵洋洋振林谷,而西江之学名天下。”[52]青原山阳明学讲会有三期主盟:第一期是五贤,包括王阳明及其弟子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第二期是胡直、王时槐等再传弟子;第三期是三传弟子郭子章(青螺)、邹元标(谥忠介)。邹元标倡导“知佛然后知儒”,吴应宾致意邹元标:“新建三间意,青原图画传。”[53]这可将青原山学脉作为发展王阳明三教三间喻的代表。据方大镇怀邹元标诗“骑牛亦可隐麒麟”[54],相当于将儒学(麒麟)隐藏于老子(骑牛),可作为以庄子为孔门真孤的先声。[55]方以智服膺郭子章、邹元标之学:“青螺举杏荆以示人”,“忠介曰:‘江河纳百川,罔不欣受,岂作二见?’”[56]据郭子章之论:“杏与荆一也,七祖与五贤一也。”[57]邹元标的江河与百川之喻不仅适用于统合阳明后学各派,而且亦可拓展至统合禅宗与阳明学,乃至诸宗教。综合来看,在方以智之前,青原山在儒学、佛教、以及儒佛互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对于已经实现药树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方以智而言,驻锡青原几乎成为他的不二之选。
方以智至青原后,“荆枯新得蘖(倒荆再发),瀑隐始通泉(瀑为药公新开)。”[58]七祖行思所植的荆树枯而复活,赋予青原山禅宗复兴的神秘启示,山水与人文均焕发生机,且交相辉映,显示出方以智对于青原山人文环境的重大影响。“不知七祖钵谁传,但见黄荆种犹活。药公采药无古今,百川到海难为深。”[59]在佛教信徒的心中,“药公”方以智无疑是七祖衣钵的继承者,飞泉新沛,枯荆复荣,更增加了方以智的威信。复荣枯荆如同“绝后重苏”的方以智,药树具体化为荆树。“荆树放光”,“东西合掌,恰度今时”[60]。“东西合掌”指儒佛合流,正奇相合,荆杏合一。“今又寓战国漆园之身而为宣尼聃昙说法,此等深心大力,何可思议乎?”[61]庄子为孔子托孤,栖身老聃之门;方以智为儒学托孤,栖身于佛门,聚众贤,兴讲会,树人才。在邹元标、郭子章的后学支持下,方以智与施闰章相砥砺,“大振传心之铎,冷灰重爆”[62],两人可视作青原山讲会第四期的主盟。“青原道场,胜冠吉州。迩药地大师驻锡,阐释宗教,远近人士及缁俗等众,译斯旨趣,如大梦忽觉、旅客乍还,各证悟本来面目,兴起赞叹。”[63]“八窗玲珑,青山屋里,禅众栖止,肃肃雍雍,千指围绕。钟板中节,三代礼乐,万仞风规,欹欤盛哉!”[64]儒学礼乐鼓舞于禅宗祖庭,佛教的钟声与儒学的铎声相合,荆杏双修之风重振:“舍身坛宇,讲此乡约,乃为药病中风吹不入之至圣。”[65]借助佛教寺庙宣讲儒学入世的着实之教,方以智部分实现了化身药树、以医王担当、为儒学托孤的理想。
方以智晚年“于枯荆下新建禅堂,愚山居士颜为‘药树’”[66],作《药树堂铭》,此铭集中展现了方以智的哲学宗教精神。笔者考察净居寺碑林,发现此碑有破损,漫漶处甚多,兹综合诸说,考订全文如下:
在天地间,谁逃寒热?炼药开炉,冬雷破雪。
种藏核仁,花飞雨血。七接揠盖,造命奇绝。
倒插生根,枯而复蘖。不萌枝上,硕果暗结。
龙渊烧淬,三番两折。夜半天明,不容齿舌。
此中山水,险崖断碣。仰空一笑,不欺时节。
诗后有行书文:“杖门托孤,永志其智。极丸学人,舍身随发。视笑公塔,扶杖游憩。睠枯荆芽,感雷雨志。爰建此堂,表笑公意。兆牂阳月,援毫以记。”[67]从实指来看,七祖倒插的荆树“枯而复蘖”,硕果暗结,仁已熟。从喻指来看,方以智久经生死锻炼,仁体蓄积的生意饱满,所炼之药已成,可以开炉济世,不负下宫之托。第四阶段的药树思想主要有四个特点,分别为:
第一,“炼药开炉”是药树思想前三个阶段的总结与升华。在第一阶段,方以智由儒转佛,引药树为奇兵,以此激发超越生死的精神。在第四阶段,方以智已是禅宗曹洞祖庭的主持、佛教宗门的领袖,在形式上,佛教由奇兵转化为正兵。在第二阶段,方以智由闭关而得悟“死是大恩人”。受困于死亡的险境,方以智不得已去面对,并被动承受,“以生死处来发药”,以死求活;而第四阶段的宗旨洋溢着生机,是方以智主动应对、担当与开拓。综合来看,方以智经历了从生到死、以死求生、从死返生、生机洋溢的过程。承接第三阶段的“还说药”,第四阶段不仅要说药,而且药已烹炮完成,炼药开炉,展现其大用。
第二,正奇互用。“种藏核仁”,药树与仁树合一,相当于以“奇”为药,医治“正”病,反之亦然。正奇互为病药,这是对于青原山荆杏双修学风的新发展,并呼应觉浪道盛的杏花与药树(儒与佛)的反叛一贯。在第一阶段,方以智引药树为奇兵,亦有被佛教同化的危险。方以智在南京闭关时,“适老父自鹿湖寄《时论》至,箴之曰:当明明善,勿泥枯璧。得六字神,实虽永锡。不肖泣曰:璧本不枯,而天故枯之。芽之已生,二芽不敢分别,谨纪此梦以禀。”[68]明明善是儒学要旨,枯璧代指佛学。方孔炤担心方以智陷溺佛教,故以儒学要旨警示之。方以智深明老父之心,禀之以“枯璧”生“二芽”,“二芽”当指“仁”(从“人”从“二”),芽已生,表明借助佛教的枯璧实现儒学生生之仁的复活;通过相反相因,由佛教的超越精神激活儒学的仁体。“所切切者,绝后苏来,随分自尽而已。”[69]枯璧生芽相当于“绝后苏来”,苏来之后,方以智要展现仁体的生机,“随分自尽”是指奉行儒学切实的伦理规范,这相当于以佛教之药救儒学生死之病。佛教是迹,儒学是神,“贵得其神,勿泥其迹。”[70]由此表明方以智坚定的儒学立场以及托孤者的内在隐忍及外在表达。神与迹分别对应奇与正、佛庄与儒、不生与生,“偏言迹,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尘。以不生灭之神寓生灭之迹,以增减之迹存不增减之神。”[71]神迹两分,则各有其病;神迹互用,可以实现互为病药。儒学泥迹,可以通过佛道的不生之神来寓居于迹,从生死学来讲,便是将佛道无生死的精神寓居在儒学的善世尽生。同理,佛道偏于无生之神,秕糠尘世之生,可以通过实际之迹来平衡佛道,从而得神迹之全。“圣人惟立中道而悬其高者,以学传神,迹偏于下而达于上,神游于下而上无上,究竟难言何上何下。”[72]这是以孔子的立场来统合三教。按照方以智的诠释,孔子不是不知死亡的视域与神化,而是综合慎重考虑神与迹的利弊之后,选择以迹传神,以学传神,悬搁死亡,罕言神化,将为学的重心放置在生生、实际之迹。以孔子的中道精神为指导原则,迹之下者,以上达激之;神之上者,以下学实之,方以智诠释的孔子神迹平衡教法源于其《东西均》的哲学思想,亦符合孔子作为“大成均”定位,并指出儒学“以神寓迹”“以无生寓尊生”的哲学发展方向。
正奇互用表现在药树思想四个阶段中两种形式的儒佛会通:第一、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佛庄援儒,儒学暂时隐退(坎陷),彰显佛庄;在充分吸收佛庄哲学宗教思想后,第三、四阶段表现为儒学真精神的复活(凸显),实现儒学回归。通过汲取佛教的超越精神,儒学的生生之几更有生意;通过儒学的“着实”与“再着实”,亦为佛教补充了入世精神。第一期主盟邹守益之孙邹匡明继承阳明学,从憨山、无念禅师游,重视儒佛会通,据他评述荆杏双修:“药树悟仁树,核种今何存。忍冬乘春发,毋忘霜雪恩。杏仁与荆沥,咀片随时吞。见性破情识,慧剑挥无痕。体仁藏诸用,兼中两足尊。”[73]由西方药树证悟儒学仁树,其转换关键点是代表生生之几的“核仁”,即是《药树堂铭》的“种藏核仁”。杏仁与荆树相蕴藏,便是以药树之“奇”救仁树之“正”,反之亦然,这是由“回互”引申的“互药”,实现正余的吞吐与成环,“咀片随时吞”。“体仁藏诸用”隐含着正余的体用关系,出自《系辞上》“显诸仁,藏诸用”,“藏”即是体吞用,用藏于体;“显”即是体吐用,体显化为用。医者根据病症与外界情况,轮换使用正奇之药,相当于以中道统摄体用,兼取儒佛(荆杏双修)。
第三,生生之几的启动。“种藏核仁”以核仁诠释儒学的仁体,如同“核”为木之亥子(亥子之间为极静而真动,如同以死求生),启动生生之几,此是富有生机的真仁之体。“在天地间,谁逃寒热?”“忍冬乘春发,毋忘雪霜恩”,第二阶段的“死是大恩人”如同核仁生生之几的启动有赖于外界雪霜、雷雨、寒热的磨练,方以智久经生死考验,闭关悟道,死处逢生,以此成就生生之几。“冬雷破雪”:冬是冬关,极静之象;雷是《震》卦,是极静而真动之象,如同木之亥子,指向生生之几。“三折肱知为良医”,核仁经雪霜而成就真仁之体,亦如铸剑的千锤百炼,即是铭文的“龙渊烧淬”,亦如孙晋所言:“甑蒸闭气,其饭乃熟。数烧数淬,大阿乃成。”[74]烧淬是锻炼神武之剑,“久淬冰雪,激乎风霆”,“三番两折”,龙渊由此更加锋利。方以智如太(大)阿神剑,成于“大炉鞲”[75];“甑蒸闭气,其饭乃熟”,如同用高压锅做饭,在气压上升、温度提高、蒸汽熏蒸等联合作用下,生米熟透;又如核仁历经风霜雨雪,后熟期完成。饭与核仁之喻均是表明方以智经历的生死磨练,生生之几不是由生直接求得,而是通过第二阶段的“死是大恩人”,以死求活,并感恩死难的经历,由此生生之几迸发。这也符合中医的观点:最有效的药是培养元气,即开掘生生之几,此是大医王用药的关键。
《药树堂铭》凝聚了方氏三代的哲学精神:“蹋完南北放杖笑,芭蕉剥死硕果活。”[76]剥尽复来,如冬雷破雪、绝后复苏,相当于方中通所言:“冬炼三时传旧火,天留一磬击新声”[77],又可追溯至方孔炤:“潜老夫曰:冬炼三时,贞所以为元亨利也。”[78]在此进一步拓展冬所蕴含的生机:隐而不显的冬相当于贞,对应于前文所论冬为“余”体之义;显发昭著的春夏秋相当于元亨利,是“正”用。当身处不元不亨不利的逆境时,可通过锤炼隐微的贞体,实现生死的转换,以此既可守节,坚贞不屈,亦可贞下起元,获得生生之几。“种藏核仁”正是蓄此生机,以待仁树的遍地成林。“邵子观牡丹于未蓓蕾之先,善喻也。冬至子半,一蓓蕾之几也。”[79]冬至是冬向三时转化的关键点,预示着生生之几的萌动,如同核仁破壁而出,从闭藏转向生生;冬至又如夜半、亥子中间、冬雷破雪,是极静到真动的转化点,并对应邵雍的元会运世思想之午会,“一元午会,人法全彰。(依邵子法,今午会中。)”[80]“青原药地既合天地万古为一身,而为午会今时说法”[81],按此而论,危中有机,明夷亦是凝聚锤炼生生之几的良机,遗民不因亡国而消沉,而应“冬炼三时传旧火”,以迎接文化大明。“天地古今”是三教的公因,可以看出方以智晚年“药天地”“药万古”的宏大愿景。
第四,由被动变为主动。“杖门托孤,永志其智”,从南京闭关至晚年建药树堂,方以智的托孤之志始终如一,“托孤在兹”[82]。在药未炼就、剑未铸成、仁未熟化、生生之几尚未启动时,托孤者当以伏藏为主,表现为对于外界恶劣环境的被动适应。药已就、太阿成、儒学之仁的生生之几启动后,托孤者应从被动转为主动,炼药开炉,展现仁体。青原山“欹欤盛哉”的钟铎之声与清初高压的政治文化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明代遗民,方以智主动彰显,预示着杀身之祸的速至,正如铭文的“仰空一笑”,方以智对死处之超然泰然,无惧危祸,由此可明方以智晚节之正。
三、应病予药的哲学基础
由引药树为奇兵,到化身药树,炼药开炉,在解决生与死(着实与超越)、淬炼托孤之志等现实问题时,方以智从佛教外围逐步进入内核,成为佛教宗门领袖。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四大思想家中,方以智对于三教文化整合、三教互补等方面思考得最广,开掘得最深。方以智的药树思想出发点是援佛庄救儒,“烹雪炮漆,偏教医活死麒麟”,即是以佛庄为药,救儒学之病,激活儒学之仁的生生之几。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亦可救治佛道之病,实现交互轮转的互药。方以智“药地”的名号因《药地炮庄》广为人知,天地正余交轮,药地(药天、药天地)不仅要救儒学,还要救三教、天地,由此显示出方以智高远的志向。当然,药树思想四个阶段反映出的方以智哲学宗教思想变化,这是药地所不具备的。药树与药地既有差异,又内在一致:“果知天地同根之大肆也,听以天地交易,日中为市,则必以灌本结实相告,不以偏枯巧蠹诳人,而药树种成林矣。”[83]天与地是大反因,天地本同根,其根为公因,公因统反因。“大肆”是交易的店铺,此处当指药铺,以天地同根为药,也就是“药天地”的寓指。天地的根本教法在于“灌本结实”,“本”是三教共同的基础,“实”指向儒学的着实根基,富有实学特色,也是方以智宗教哲学的起点与归宿。药树可医治佛教超越的偏枯之弊、庄子齐物论的巧蠹之弊,相当于烹炮麒麟之药,医救雪、漆之病;义理层次表现为以公因为药,医治反因之病。果能实现反因之间的轮转、反因与公因的轮转,且能推广至天地,则“药树种成林矣”,显示出药树思想应用的普遍性。
如上所述,药树已体现出对症下药的思想,如超越为着实之药,死为生之药,反之亦然,这可统称为“应病予药”。方以智深谙医理,且能悬壶济世,“以药囊禅钵转侧苗峒”[84]。要做到应病予药,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明药性,其二是辨病症。“明者知其产,观其色,得其气味,而性可识也。不识其性,又安所讲君臣炮制乎?”[85]要炮制适合病症的药,须先明药性,下文以“大青龙汤”为例说明。[86]此方用药如下:麻黄(六两)、桂枝(二两)、甘草(一两)、杏仁(四十枚)、生姜(三两)、大枣(十枚)、石膏(如鸡子大)。适用病症,“大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燥者”。病与药的相应关系如下:第一层,君臣:麻黄为君,桂枝为臣:“麻甘温,桂辛热,寒则伤荣,以甘缓之;风则伤卫,以辛散之,故麻为君,桂为臣也。”麻黄与桂枝各有其药效,但亦各有其不足,两用之,则能扬长避短,交相助益。第二层,佐药。分两组:甘草与杏仁;生姜与大枣。甘草与杏仁佐君,“甘草甘平,杏仁甘苦,苦甘为助,佐麻黄以发表”;生姜与大枣佐臣,“大枣甘温,生姜辛温,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第三层,使药。石膏。“石膏辛甘微寒。夫风,阳邪也;寒,阴邪也。风伤阳,寒伤阴,阴阳两伤,非轻剂所能独散也,必须轻重之药同散之,是以石膏为使,而专达肌表也。”在正奇关系统领下,可分出三组主要关系:君与臣;君臣与佐,包括佐君与佐臣;(君臣佐)与(使)。[87]以此理念转用于宗教,其表现为:
皆病也,皆药也,有总杀之药,有杀半之药,有公容之药,有不容之药。然正当明其正药奇药,毒轻毒重,君之臣之,佐之使之。神医之诊,惟在当不当耳。[88]
方以智应病予药的哲学基础之一在于皆病皆药,即承认病与药的普遍性。方以智着眼于三教的总体性,而不是独尊儒学之一教。三教“皆病”指各教均有缺陷;三教“皆药”指各教均有优长。儒学应正视其教法之不足,如死亡视域的关闭、面对生死抉择时的懦弱退缩等,可通过佛教涅槃、庄学齐生死之药补救;尊生、着实是儒学的优势,以此为药,可以救治佛教着空、庄学虚无之病。皆病皆药的思想有利于打开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闭传统,从而开放性吸收佛道思想,实现儒学创新发展,亦有利于推动佛道的世俗化。
方以智应病予药的哲学基础之二在于辩证用药,药分正奇,善用奇药,这在上一节已有说明。“正药十九,奇药十一,全正藏奇,则盐水皆可吐下矣。”[89]若仅用正药,固守传统医方,沉疴痼疾易产生耐药性,减弱正药的疗效;而奇药有奇效,当然,奇药须运用得法。从用药量来说,正药十分之九是主体,而少量奇药的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奇”相当于“偏”,“教亦多术,应病予药,不妨偏言。”[90]以病症为依据,从根本处认识病因,方能用药得当。偏方能达到超越正方的效果,其深层原因在于知症:“大宗师应病予药,神在知症”,“知则不为一切琦辨奥理所惑,而我可以转之”[91]。如上述大青龙汤,大宗师(大医王)用药时,君臣佐使,各有其用,综合辩证,并根据病症调整。转用到哲学宗教,大宗师是指深刻把握各教精义的大思想家,他根据各教出现的问题,综合运用各种教法来医救。具体到生死问题,传统儒学多从生生的视域言仁,这是儒学的正药十九;在面对刑场生死考验时,方以智以超越的精神打开死亡的视域,这是奇药十一。从呼应原始儒学来看,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可理解为“全正藏奇”,即将死之奇藏于生之正。因此,在常态时,正显奇藏,表现为只谈生,悬搁死。然而,在应对危机时,需要将孔子的所藏显赫出来,以奇为药,由此可说方以智真正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生死学。[92]
由生死学拓展,中国儒学传统重视世俗的价值(正),缺乏超越的精神(奇),针对这种状态,以奇为药,可通过超越补救着实:“全能用偏”,“君师之责,安顿三根;刍狗青黄,无非神化。当前碧落,一乡约所也。讲各安生理之生即无生,则佛魔掩泥砥属矣,贵图天下太平。”[93]这相当于在坚守儒学着实传统的基础上,开掘出儒学的超越精神。儒学超越的进路(碧落、无生)隐藏在平实的“五伦《六经》”(乡约、各安生理、“中土杏花知正命”)。经此疗教,儒学不仅不缺乏超越,而且能够涵盖超越,在日用伦常中展现超越的密义。“各安生理之生即无生”与药树思想第一阶段“生即无生尽此生”均是吸收了佛教“无生”的奇药,作用于儒学各安生理、尽此生的传统,从而使得儒学在着实中洋溢着超越的精神。
方以智应病予药的哲学基础之三在于公因。公因指向三教的共同基础,以此作为三教互救的起点与归宿,此药可称作“公容之药”(《道德经》的“惟容乃公”),如吴应宾所言:“私者,病也;公者,药也。”[94]“私”可指三教互不相通的独自发展,“公”指三教作为宗教的共性,由此共性而派生出殊性,“不知天地人之公因,即不知三圣人之因”[95]。“好名也,养生也,畏死也,此天地奉三圣人之姜枣引也。生引死引,要归名引。”[96]三教的立教者(三圣人)各有所主:儒学重在世俗化的着实名教,佛道重在超越生死,这是三教的主要分别处。“天地”作为三教公容的基础,在终极处“无分别”,以此“无分别”奉三圣人,而成三教之“分别”。“天地”可理解为人类生存的自然宇宙,人生天地间,天地是各宗教的共同出发点。儒学的短板表现为死亡视域的关闭,明清之际,如饱读诗书的钱谦益等儒者因求生而畏死,因畏死而屈节。方以智与此不同,如其自祭文“生即无生尽此生”,他以佛教的涅槃精神为君药,超越生死;如其自祭文“蒙庄氏日以齐生死、一殀寿为言”,以庄学齐生死为臣药,从而不畏死、保全节,捍卫儒学真精神。综合君臣之药,通过庄子的“生引”与佛教的“死引”,归结在儒学的“名引”;换言之,烹炮佛庄之药,疗教儒学名教之病。在这一过程中,佛庄之病亦可得治,“孤言生即无生,则盗即不盗矣。”[97]以儒学的尊生可以避免将庄学的“齐生死”陷入诡辩、将佛教的涅槃沦为沉空寂灭,相当于以儒学之药医救佛庄之病。“不知五伦《六经》之道器,即万古於穆之法身。必骑千里马,寻青又青之山,告以足下之土石是矣,犹不信也。”[98]儒学的名教即是佛教的法身,佛教脱离世间法,别去寻求一个超越的远山,却不知远山就在脚下,灵山就在心中,超越就在着实中,由此救治佛教追求超越玄空之弊,相当于以儒学之药救佛教之病。综上,列表如下:

从公因反因来看,“无分别”是公因,“分别”是反因:“知公因在反因中者,三教百家、造化人事毕矣。”“天下之至相反者,岂非同处于一原乎哉?”“并育不相害,而因知害乃并育之几焉;并行不相悖,而因知悖乃并行之几焉。”[99]按此,方以智疗教“三教百家”的指导思想要点有二:其一,善于运用反因。儒学重生与佛道重死为反因,儒学尊生避死与庄子齐生死为反因,儒学着实与佛道超越为反因。常人多以“反因”相害相悖,导致儒佛道之间紧张对峙;方以智善于运用反因,创造性地将相反的事物互补互救,从而实现反因之间的并育并行:“道同法异,各别溪山;理学宗教,激扬攻玉。”[100]由此在充分发挥三教之长的基础上,增强中国文化的整体合力。从儒学本位立场看,这相当于激活了儒学超越生死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儒学面临危机时尤为重要。其二,公因与反因轮转,相互补救。相反者同出一原,这一原便是公因,三教的公因便是天地、公容、同道。反因着眼于分别,公因则着眼于无分别。“无分别即分别,分别即无分别,回互明矣。”[101]“回互”之意是公因与反因的相互轮转,公因在反因中,反因亦在公因中,这种医救三教的方式极具原创性与现实意义。三教合一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矛盾:如果“合一”是以消除三教差异为代价,寻求三者的公约数(公容),比如儒学的入世与佛教的出世相交,交集会很小,甚至是空集,那这样的三教合一显然行不通。若以三教之一教为主,统摄其他两教,从而达到“以一统二”,则被统摄者显然不能接受。如何既保证三教的特色,又能使三教在“三教合一”中均有所受益,这是明代“三教合一”的结穴。要突破这一结穴,需要对于三教各家均有深刻了解与体证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无疑具备这些条件。据施闰章记述方以智晚年三教之论:“教无所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区分,其实一宅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102]方以智以殊相为实际,尊重三教的差别;以互通为指向,致力于三教的对话;以互用为手段,在三教对话中各有受益。这突破了王阳明以儒学统佛道的三间喻,既尊重三教各自的特色,容忍三教差别;又能扬长避短,相互补救,在本原处、终极追求处以公因的“无差别”共通。从形式上看,较之于王阳明,方以智将儒学与佛道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貌似有损于儒学独尊;从实际效果来看,正是通过平等的互通,使得儒学能够开放性吸收佛道超越死亡的哲学宗教思想,打开儒学死亡视域,反哺儒学的生生仁体。
由公因反因还可引出张弛之法,“明公因反因之故,而益叹一张一弛之鼓舞者天也。弓之为弓也,非欲张之乎?然必弛之养其力,乃能张之尽其用。”“由邵子四分用三、摄三于一推之,天地炼物于冬,而长养之于春夏秋”[103]。张相当于“正”用,弛相当于“余”体,张弛为反因,张弛相养相用:弛以养张,非弛不能张;张以用弛,非张不能弛,这使得互为反因的儒学与佛庄的联系更加密切。张弛关系的内在逻辑是一张一弛,在量上是“张三弛一”,总体为四;从四时喻来看,冬为一养之弛,春夏秋为三用之张,张弛、常偶对应正奇(余),以此相通邵雍“四分用三”的思想。反映到时间轴上,便是张与弛的更迭。儒学多用张教,罕用弛法,“偶发惊地之丰隆,常用平和之朗日;一炼雪霜之刊落,三施煦育之长养。王法也,师教也,神道也,皆不能出此张弛也。”[104]从应用范围来看,正奇张弛不仅有助于方以智正视生死、披缁后保持儒学的真精神,而且能上升到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推广到政治(王法)、教育(师教)、宗教(神道)。结合中医用药随时令变化,“冬令主闭藏,不宜疏泄”,明亡后,如果遗民再舒张,将速致杀身之祸,即“煦育之长养”不能展开;在此情况下,方以智另辟蹊径,转用弛法,即“雪霜之刊落”的路径,也就是从冬入手,“冬炼三时传旧火”,以余炼正,以弛炼张,从而在隐忍中蓄积爆发的生机,这是儒学在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形态。对应公因反因的轮转,张弛的公因便是“故(根本因、所以)”,以此作为更高层次的体,“知全张全弛之故,而立张三弛一之法,以享张一弛三之用。”[105]叠加这层体用关系,“故”为体,“张三弛一”为用,以体驾驭用,并在更高层次中轮转体用,这显示出在掌握“故”之后,大医王“应病予药”的自在自如,亦体现出方以智在三教会通中贯彻了理性精神,是以深刻的哲学思考为基础,从而使得三教互救的思想更为稳固。[106]公因、故、生生之几,均显示出方以智超越一般的医者,“盖医能医病,药地能医医,是曰医王。”[107]总体来看,方以智不仅要治病,而且还要救医,以医王担当,这显示出方以智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厚重的学术使命。药与病为对待的反因,通过第三阶段的“病药俱忘”,实现反因到公因的超越;通过“还说药”,从公因的超越返回反因。如果“药病俱忘”尚有大乘空宗的余韵,而“故”的引入则将其归为追根溯源的哲学思考,服务于实有层次的致用。通过公因与反因的轮转,儒佛庄之病均得救治,三教关系更为密切,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
以上三个哲学基础均依赖于正余关系:基础之一是病药为正余的普遍性;之二是善用奇药,即善用余,药树思想的四个阶段都是如此;之三是两层正余关系———反因之间、反因与公因。当正余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有病)时,可通过另一方医救(作药)。正余回互,余转为正,正亦转为余,病药关系亦随之回互。这种方法主要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相互疗教,医救之药亦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显示出这一体系的封闭性以及创新的有限性。但是,如果结合“借远西为郯子”[108],则方以智的“应病予药”思想体现出开放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现代性精神。回顾药树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在起点,儒学死亡视域的思想资源可谓贫乏之极,儒学在明亡危机中多处于被动状态,儒者在应对生死考验时显得力不从心。在融合明代学术与家学“三教独立”与“三教合一”传统基础上,通过吸收佛道对于死亡的正视与超越,结合人生实际之亲证,方以智创造性提出并发展了药树思想,致力于以佛道为药,救治儒学之病,充实儒学的宗教思想。通过三教互救互补,不仅有助于儒学的宗教化发展,而且佛道亦可吸取儒学入世、生生的思想资源,以儒学之着实补救儒佛之超越,促进佛道的世俗化转型,这亦是当今宗教发展的重要趋势。三教在独立发展中相互统合,实现交相受益的三教合一,这是方以智宗教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精神遗产。
综上来看,在药树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若方以智以死终结,均不失节,方以智的气节不因时因境改变而有所动摇,内在思想与外在行实一致,由此可证方以智晚节之正。相对于刘宗周的绝食而亡,方以智的死更富有曲折性与使命感:刘宗周的死节代表了对于旧朝的坚守,为坚守付出生命;方以智的死节重在文化的使命,在中国文化饱受摧残之后,致力于冷灰重爆,迸发生生之几,展现出面向未来的使命与担当。方以智后死托孤,从广西刑场到青原净居,屡经生死锻炼,由对死亡的被动承受到主动担当,乃至炼药开炉,努力实现托孤者的使命。通过后死,方以智打开了儒学的死亡视域,锤炼了生生仁体,淬砺了托孤之志,主动应对危机,完成了大儒的使命,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气节、奋发精进的风骨。最后引一则材料佐证晚节:“辛亥,粤难作,师闻信自出曰:‘吾赊死幸过六十,更有何事不了?’终日谈笑,处之坦然。”“师因法救法,剥烂会通,彻上彻下,穷尽差别”,“岂非旷代一兴者乎?天盖子以百淬托孤别路,资此集大成者也。”“万世而下自有知者。”[109]“因法救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药树,主要内容是以佛庄救儒学,补足儒学的死亡视域;“剥烂”如同“芭蕉剥死硕果活”,以死求生,打通生死。从不惑之年到耳顺之年,方以智的药树思想已臻纯熟,以佛庄救儒的学术使命已经完成,谈笑与坦然显示出使命完成后的轻松与愉悦、对死亡的澹然与从容。“苦心如此,供养后世,谁得而知之?”其回答便是“万世而下自有知者”,这显示出其学能够为后世认可的坚定信念。
[1]《年谱三》,《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22-1423页。
[2]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册),汪培基、徐新育、张泽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90页。
[3]杜维明:《儒教》,陈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4]张学智:《宋明理学中的“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5]方以智内在思想发展的研究有赖于其哲学著作的研读与整理,余英时作《方以智晚节考》时,“其已流布者如《药地炮庄》余亦未尝获见”。(《方以智晚节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8页。)由于当时方以智的《易余》等重要哲学著作尚未流布,受制于客观条件,内外一致的综合研究不能深入展开。
[6]方以智:《知言发凡》,《易余》卷上,《易余(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7]方以智:《薪火》,《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35页。
[8]方以智:《附录》,《易余》,《易余(外一种)》,第215页。
[9]包璿:《青原曼老人》,《诗》,《青原志略》卷十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10]孙晋:《药树堂碑文》,《碑记》,《青原志略》卷四,第113页。
[11]计六奇:《举朝醉梦》,《明季南略》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461页。
[12]方以智:《独往》,《遗民诗》,卓尔堪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67页。
[13]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一,《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61页。
[14]方以智:《马帅见迮招浔爵书重历刀头说此一偈》,《无生寱》,《浮山后集》卷一,《方以智全书》第10册,黄山书社,2019,第243页。师(狮)子尊者是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遭外道陷害,罽宾王秉剑,“至尊者所,问曰:‘师得蕴空否?’祖曰:‘已得蕴空。’王曰:‘离生死否?’祖曰:‘已离生死。’王曰:‘既离生死,可施我头。’祖曰:‘身非我有,何恡于头!’王即挥刃,断尊者首。”(《五灯会元》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方以智以师子尊者类比自己的处境与抉择:清军马帅环刃如同罽宾王秉剑,方以智借助师子尊者出离生死的精神来面对险境,由此可知方以智的气节洋溢着佛教超越生死的精神。方以智此时并未披缁,这应得益于吴应宾的教诲,说明方以智此时不仅熟知佛教经典,而且在危机时刻能够应用禅宗精神实现全节,由此可见方以智的佛教基础之深厚。
[15]方以智:《重絷至平乐法场逼以袍帽只吼涅槃而已》,《无生寱》,《浮山后集》卷一,《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242页。荒木见悟认为:“方以智当初归向佛法,确实是基于逃禅的动机,但与觉浪道盛的相遇,却仿佛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思想转机。之后,方以智受到父亲与外祖父吴观我的影响,继续研究《易经》,至于‘废眠食、忘死生’的地步,但结果他所到达的境界,却是‘《易》理通佛氏,亦通老、庄。’”(荒木见悟:《觉浪道盛初探》,载《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廖肇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此论有三个问题:第一,还原方以智刑场破生死关的顺序,披缁的动因应是清军将领厌恶头陀,方以智以头陀状出,以求速死,但仍逼以袍帽,方以智由此披缁。方以智披缁的过程可以说与“归向佛法”无关。第二,方以智与觉浪道盛相遇,是在平乐破生死关三年之后,“初,吾乡方密之自岭外薙染还里,皖开府李中丞问召问:‘信已出家耶?’方曰:‘信矣。’曰:‘若信,吾指汝一师。’问为谁,曰:‘觉浪和尚也。……是真和尚也,固当师。’密之闻言,即至天界礼杖人为师”。(钱澄之:《住寿昌观涛奇禅师塔铭》,《田间文集》卷二十三,《钱澄之全集》之六,黄山书社,1998年,第456-457页。)方以智之所以言“信”,是为了婉拒清廷招抚。第三,“之后,方以智受到父亲与外祖父吴观我的影响”,应是方以智在平乐前,已深受吴应宾影响;吴应宾于崇祯七年(1634年)去世,方以智在平乐时是1650年,何来“之后”受吴应宾影响?以上三处可证荒木见悟之说之误。
[16]方以智:《辛卯梧州自祭文又诗一首》,《无生寱》,《浮山后集》卷一,《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245页。据此可知,方以智在梧州时形成药树思想,此时尚未拜入觉浪道盛门下,可能更多受到吴应宾影响。吴应宾已有病与药思想的雏形,参见吴应宾:《性善篇》,《宗一圣论》卷上,《宗一圣论古本大学释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23页。前期研究成果多将方以智的药树思想关联《药地炮庄》与觉浪道盛指点方以智的“一茎药草”,两者均指向觉浪道盛。如觉浪道盛《寄示无可智公》“当以破篮一茎,慎自变化之”。据劳思光所论:“所谓‘破篮一茎’盖用文殊与善财采药之寓言。文殊拈一茎草谓只此能杀人能活人;觉浪以此‘能杀能活’喻曹洞宗旨。而函中特标此义,盖又暗示对密之宏大教义之期望也。及密之入门,觉浪更作‘破篮茎草颂’,前系长序,重说此义。”(劳思光:《〈方以智晚节考〉及〈补正〉读后感》,载《冬炼三时传旧火———港台学人论方以智》,邢益海主编,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65页。)劳思光之论可能是颠倒了时间顺序,正确顺序应是:觉浪道盛作《破篮茎草颂》在先,《寄示无可智公》在后,首说此义于“癸巳(1653年)孟冬书付竹关”,(《破篮茎草颂》,《天界觉浪道盛全录》卷十二,《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20页。)方以智破关,庐墓三年后,1658年再至庐山(1652年曾至庐山),觉浪道盛作《寄示无可智公》,重申此义。在功效上,药草相当于药树。一茎草能活人,通过闭关竹轩,方以智从枯璧中获得生机。
[17]释道世:《杂异部第五》,《神异篇第二十》,《法苑珠林》,《法苑珠林校注》,周叔迦、苏晋仁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862页。
[18]释道世:《发愿部第十一》,《受戒篇第八十七》,《法苑珠林》,《法苑珠林校注》,周叔迦、苏晋仁校注,第2577页。
[19]方以智:《世出世》,《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65页。
[20]方以智:《易余小引》,《易余》,《易余(外一种)》,第2页。
[21]方以智:《中告》,《易余》卷上,《易余(外一种)》,第49页。
[22]从体用来看:冬之“余”体的凝聚是翕,三时之“正”用的舒张是辟,如同四时轮转,正余的体用关系亦可以相互轮转,互为体用。(张昭炜:《正余的吞吐成环及双向开掘———论方以智的体用观及其创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生死轮转还可以通过“化”字的解释来说明,化字的古字从“倒人”,后发展成左边的正人(亻)与右边的倒人(七),“一生一死之名也,制字者苦心哉!”(《译诸名》,《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庞朴注释,中华书局,2016年,第233页。)化字,“从倒人,人终必化;后加人于旁作化,则生死之道尽此。”(《尽心》,《东西均》,同上,第132页。)按照制字者的苦心,生与死分别是人的正与倒,两者相反,通过颠倒轮转,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以死化生,以生化死。方以智在刑场上如同文天祥、刘宗周那样以“无生”的超越精神死亡;在此基础上,方以智还有第二阶关系的展现,即再返回着实的“尽此生”,以此实现后死托孤的使命。
[23]方以智:《出世诀》,《无生寱》,《浮山后集》卷一,《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249页。
[24]方以智:《涅槃矢》,《建初集》,《浮山后集》卷四,《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315页。
[25]施闰章:《无可大师六十序》,《施愚山集(一)》,黄山书社,1993年,第166页。
[26]方以智:《仁树楼别录》,《书院》,《青原志略》卷三,第90页。
[27]方以智:《与藏一》,《书》,《青原志略》卷八,第190页。
[28]方以智:《首山茶筵示众》,《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二,《方以智全书》第3册,第116页。
[29]按照荒木见悟阐释的觉浪道盛烈火禅及其对方以智的影响,要点有三:(一)炮庄,炮为烧意。(二)托孤的传法,即将庄子作为儒学的教外别传。(三)三极辩证法,也就是庞朴先生讲的“一分为三”。(《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研文出版社,2000年,第266-274页;中文介绍著作可参看张崑将:《荒木见悟〈忧国烈火禅〉之评介》,载《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荒木见悟与近世中国思想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365-367页。)对此回应如下:(一)炮固可解释为“烧”,但更侧重药,炮之意还涉及药性的搭配,如正药奇药、以及君臣佐使等。(二)托孤论是方以智从觉浪道盛接受的核心思想。《药地炮庄》的两大思想来源分别是吴应宾与觉浪道盛,吴应宾的庄学影响不可忽略。(三)三极辩证法主要来源是方氏易学,如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合编》等,不能将其归为觉浪道盛所传。另外,方氏家学亦重视火论,方以智怒化烈火的思想亦有源自方大镇、方孔炤的家学传统。(张昭炜:《方以智“怒化生生”的哲学精神》,《哲学与文化》2021年第9期。)
[30]张昭炜:《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6页。
[31]方以智:《奇庸》,《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庞朴注释,第199页。
[32]方以智:《药室说》,《序说》,《青原志略》卷五,第126页。
[33]方以智:《墨历岩警示》,《冬灰录》卷一,《方以智全书》第3册,第211页。
[34]孙晋:《药树堂碑文》,《碑记》,《青原志略》卷四,第114页。
[35]方以智:《和陶饮酒》,《无生寱》,《浮山后集》卷一,《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252页。
[36]据《维摩诘经·佛国品》,“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应病与药”。医疗生之病,须用死之药。生死为人生根本,生死关一透,利害、人我等“我见”便迎刃而解。“昔维摩示疾毗城,以病作医,欲去众生无始、爱见、攀缘、妄想之业。夫此四大变化,诡异如梦影空华,孰能一一按其症候哉?我谓维摩神力,亦不过欲众生悟此生死妄因,而自得解脱耳。”(方以智:《药室说》,《序说》,《青原志略》卷五,第126页。)以生死为虚妄,以无生死为真实,这吸取了禅宗之“无”的精神。“其奈无始结习,欲忿为累。横执我见,油面胶投。然则以毒攻毒,安可少哉!”“《维摩经》曰:‘众生不病,则我不病。我若不病,则众生之病永不可除也。’能无然疑作乎?置之死地而后生乎?”(孙晋:《药树堂碑文》,《碑记》,《青原志略》卷四,第113页。)“我见”执着于“我”相,纠缠在结习、欲忿等,佛教“超越”之药是破除“着实”的“欲忿”之累与“我见”之胶。生死为正余,死地即是生处,如《坤》《复》之际,极阴中迎来一阳萌动,由此实现“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有生死”与“无生死”为正余:佛教将常见“有生死”之“正”视为“妄因”,如梦中影,空中花;真实之“余”在于“无生死”,悟得真实,在“无生死”中驾驭“有生死”,并实现“尽生死”。
[37]孙晋:《药树堂碑文》,《碑记》,《青原志略》卷四,第113页。此处须注意“因随所在”,按此理解,“药地愚者”之前的“药地”当为地名,其形式相当于“浮山愚者”之“浮山”,从积极意而言,“有人即病,病亦是药”,(《反因》,《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第141页。)正是由于儒学之病的存在,才使得药有必要;换言之,无病则无须用药。病与药可视作正余关系;再叠加一层本无病药,由此形成两层嵌套的正余关系:(病—药)—(本无病药)。
[38]张昭炜:《方以智“余”论》,《哲学动态》2020年第6期。从积极意而言,“有人即病,病亦是药”,(《反因》,《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第141页。)正是由于儒学之病的存在,才使得药有必要;换言之,无病则无须用药。病与药可视作正余关系;再叠加一层本无病药,由此形成两层嵌套的正余关系:(病—药)—(本无病药)。
[39]方以智:《药地易简约》,《冬灰录》卷一,《方以智全书》第3册,第208页。
[40]方以智:《附录》,《易余》,《易余(外一种)》,第215页。
[41]方以智:《中告》,《易余》卷上,《易余(外一种)》,第49页。
[42]方以智:《总论中》,《药地炮庄》,《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48页。横如正,为横摄,为生,为活;纵如余,为纵贯,为死,为杀。横纵如显隐,显微无间;此是内在贯通;与交轮横纵十字打开,生死兼收,此是外在拓展与撑开。
[43]方以智:《辛卯梧州自祭文又诗一首》,《无生寱》,《浮山后集》卷一,《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243-244页。
[44]方以智:《总论中》,《药地炮庄》,《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48页。横如正,为横摄,为生,为活;纵如余,为纵贯,为死,为杀。横纵如显隐,显微无间,此是内在贯通与交轮;横纵十字打开,生死兼收,此是外在拓展与撑开。
[45]方以智:《大宗师第六》,《药地炮庄》卷三,《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275页。
[46]张昭炜:《方以智“怒化生生”的哲学精神》,《哲学与文化》2021年第9期。
[47]马其昶:《吴观我先生传第三十四》,《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2013年,第91页。
[48]安徽博物院编《方以智文物集萃》,安徽美术出版社,2021年,第140页。
[49]方以智:《辛卯梧州自祭文又诗一首》,《无生寱》,《浮山后集》卷一,《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244页。
[50]觉浪道盛:《复方潜夫中丞》,《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二十七,《嘉兴大藏经》第34册,第21页。
[51]邹元标:《重修青原缘起》,《疏引》,《青原志略》卷七,第166页。
[52]施闰章:《游青原山记》,《游记》,《青原志略》卷六,第138页。
[53]张昭炜:《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47页。
[54]方大镇:《怀邹南皋总宪》,《青原志略》卷九,第238页。
[55]方以智晚年有“蝴蝶且吞金翅矣”:“蝴蝶”指庄学;“金翅”指佛学。(《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第547页。)这可视为方以智正余吞吐与成环的思想在宗教互通融合的应用。按此,庄学与佛教相吞吐,儒学与佛道相吞吐,从而有利于儒学开放吸收佛道的死亡关怀。
[56]方以智:《青原山水约记》,《游记》,《青原志略》卷六,第140页。
[57]郭子章:《荆杏双修引》,《青原志略》卷七,第158页。
[58]李元鼎:《游漱青三叠》,《诗》,《青原志略》卷十一,第317页。
[59]徐缄:《青原山新瀑布歌呈药地大师》,《诗》,《青原志略》卷十一,第310页。
[60]方以智:《致青原笑和上》,《书》,《青原志略》卷八,第183页。
[61]余飏:《寄药地尊者》,《书》,《青原志略》卷八,第188页。
[62]方以智:《青原山水约记》,《游记》,《青原志略》卷六,第140页。
[63]焦荣:《青原未了缘引》,《疏引》,《青原志略》卷七,第173页。
[64]孙晋:《药树堂碑文》,《碑记》,《青原志略》卷四,第113页。
[65]方以智:《约药》,《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82页。
[66]《药树堂文殊善财画像》,《杂记》,《青原志略》卷十三,第378页。
[67]综合《庐陵县志》(卷二十七,民国九年刻本,第50页。)及青原山净居寺现存碑刻。据民国《庐陵县志》:“《药树堂铭》,存。碑在青原山药树堂,堂为药地老人建。老人明季遗老方以智,字密之。碑高三尺许,广一尺六寸许,字径一寸三分许。行书,古崛奇劲,幽愁怨结流露笔底,完好可搨。”(《艺文》,《庐陵县志》卷二十七,民国九年刻本,第50页。)如“险崖”,民国县志误作“险岩”。新修的《青原山志》亦收录此文。(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285页。)此铭为《方以智晚节考》收录,有讹阙,如“雨血”讹为“雨雪”,此处以“血”代“雪”,更能显示明亡铸就的血道场以及方以智经历苦难;“烧淬”误作“浇淬”。(余英時:《方以智晚节考》,第209页。)
[68]方以智:《象环寤记》,《易余(外一种)》,第227页。此处可进一步展开成方以智的全仁全树思想,参见《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第529-535页。
[69]孙晋:《药树堂碑文》,《碑记》,《青原志略》卷四,第113页。
[70]方以智:《象环寤记》,《易余(外一种)》,第216页。
[71]方以智:《神迹》,《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庞朴注释,第220页。
[72]方以智:《神迹》,《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第227页。
[73]邹匡明:《荆杏双修》,《诗》,《青原志略》卷九,第237页。
[74]孙晋:《药树堂碑文》,《碑记》,《青原志略》卷四,第114页。
[75]方以智:《象环寤记》,《易余(外一种)》,第216-217页。
[76]左錞:《呈药地大师》,《诗》,《青原志略》卷十,第286页。
[77]方以智:《师诞日侍子中通请上堂》,《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一,《方以智全书》第3册,第87页。
[78]方孔炤、方以智:《系辞下传》,《周易时论合编》卷十一,《周易时论合编》,中华书局,2019年,第1221页。
[79]方孔炤、方以智:《系辞下传》,《周易时论合编》卷十一,《周易时论合编》,第1251页。
[80]方以智:《慕述》,《合山栾庐占》,《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370页。
[81]余飏:《寄药地尊者》,《书》,《青原志略》卷八,第188页。
[82]方以智:《青原山水约记》,《游记》,《青原志略》卷六,第140页。
[83]方以智:《中正寂场劝》,《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88页。
[84]戴迻孝:《合山栾庐诗跋》,《合山栾庐占》,《方以智全书》第10册,第373页。
[85]方以智:《古方解》,《通雅》卷五十二,《方以智全书》第6册,第554页。
[86]同上,第570-571页。
[87]在上述三组正奇关系之外,还应注意时令,如麻黄汤:“前哲谓冬不用麻黄,夏不用桂枝,盖以冬令主闭藏,不宜疏泄;夏令本炎热,不可辛温。《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之说’也,该通者察之。”(方以智:《古方解》,《通雅》卷五十二,《方以智全书》第6册第570页。)根据病症的变化,还应变方,以伤寒名方小柴胡汤为例,正方为“柴胡(八两)、黄芩(三两)、人參(三两)、甘草(三两)、半夏(半升)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变方为:“胸烦不呕,去夏、参,加括蒌实一枚。渴者,去夏,加参一两五钱,括蒌根四两。腹痛者,去芩,加芍药三两。胁下痞,去大枣,加牡蛎四两……”(同上,第573页。)这可以关联方以智的“时中”思想。
[88]方以智:《约药》,《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72页。
[89]同上,第182页。
[90]方以智:《三冒五衍》,《易余》卷上,《易余(外一种)》,第32页。
[91]方以智:《大宗师第六》,《药地炮庄》卷三,《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256-257页。
[92]正与余的反对关系呈现为六象十错综,“对无不反,反无不克,克无不生”,“能死者生,狥生者死”。(《反对六象十错综》,《易余》卷上,《易余(外一种)》,第77页。)这可综括为对立统一关系。通过与古希腊哲学的对比来说明生死的正余关系:哲学精神是哲人行动的决定力量,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其哲学精神在于灵魂不朽,按照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论证,“如果生与死是对立的,那么它们相互生成”,“生者来源于死者”。(柏拉图:《斐多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3-65页。)生死在对立中错综,死不再是消积意义上的毁灭,而是积极意义的面向新生,方以智由此可以在理性上对死亡处之泰然。由冬与三时之喻引申,四时轮转蕴含了生死轮转,死必能获得新生,如同冬是春的前奏。冬向春夏秋转换的关键点在于一阳生的冬至,由冬至可启动生生之几,通过“冬炼三时”,以死炼生,这正是方以智晚年哲学精神的指向,由此亦可证方以智晚节之正。
[93]方以智:《易余目录·约药》,《易余》,《易余(外一种)》,第13页。
[94]吴应宾:《致知下篇》,《宗一圣论》,《宗一圣论古本大学释论》,第35页。
[95]方以智:《所以》,《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庞朴注释,第306页。
[96][97]方以智:《约药》,《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80页。
[98]方以智:《中正寂场劝》,《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84页。
[99]方以智:《反对六象十错综》,《易余》卷上,《易余(外一种)》,第76-77页。
[100]方以智:《易余目录·约药》,《易余》,《易余(外一种)》,第13页。
[101]方以智:《约药》,《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81页。
[102]施闰章:《无可大师六十序》,《施愚山集(一)》,黄山书社,1993年,第166页。
[103]方以智:《张弛》,《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庞朴注释,第278页。
[104]方以智:《约药》,《易余》卷下,《易余(外一种)》,第174页。
[105]方以智:《张弛》,《东西均》,《东西均注释(外一种)》,庞朴注释,第280页。
[106]方以智对生死之“故”的阐发集中在《易余·生死故》,与之相应者为《东西均·生死格》。参见张昭炜:《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第419-428页。
[107]文德翼:《补堂炮庄序》,《药地炮庄》,《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5页。
[108]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物理小识》,《方以智全书》第7册,第101页。
[109]吴道勋:《正宗住持》,《法谱》,《浮山志》卷三,黄山书社,2007年,第50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12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